如何立足创新创造 构建共同未来? ——写在2024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孙远钊发表,[专利]文章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于2024年1月公布了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知识产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立足创新创造,构建共同未来”(IP and the SDGs:Building our common future with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1]巧合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一词,表示“新质生产力是以新产业为主导的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两个月后,他又对“新质生产力”作出进一步阐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之‘新’,核心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将科学研究的最新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先进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中,不断创造新价值。”[3]上述观点分别从国际和国内宏观视角点出了当前亟需专注的方向和努力的重点,结果则是“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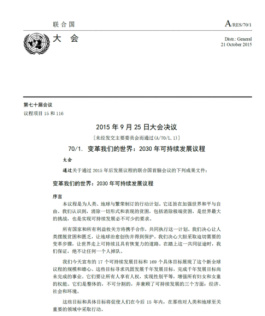
2015年9月25日举行的第70届联合国成员国大会以全票通过了一项事关地球未来生态发展、迫切需要正视和持续关切的重大决议。[4]该决议支持稍早时由联合国首脑会议(峰会)出台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行动计划,希望在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努力下,于2030年达成17个总目标,包括:(1)无贫穷;(2)零饥饿;(3)良好健康与福祉;(4)优质教育;(5)性别平等;(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10)减少不平等;(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13)气候行动;(14)水下生物;(15)陆地生物;(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以及(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上述计划设置的15年期限已经过半。联合国各成员国通过这项决议时,全球经济刚从2007-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中复苏,蓄势待发准备跃升(这也是通过这项议程的重要背景之一)。然而,仅在四年后,全球各地就爆发了新冠病毒疫情,导致至少三年的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受到疫情的干扰,全球无数的产业发生“断链”,并导致急遽的、普遍性的通货膨胀,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更加剧了上述问题。迄今为止,人类还无法预见全球性通胀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走出通胀的世界经济又将何去何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缓,则使情况更加扑朔迷离。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在2024年1月9日公布的年度“旗舰报告”《全球经济展望》(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中总结指出:“本应是全球发展突飞猛进的十年将近过半,但全球经济2024年底交出的答卷将令人遗憾——这成为过去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最慢的五年。”[5]言外之意,前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的多数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届期能否达成仍未可知。尤其是对于一些迫在眉睫的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等),各国更需要齐心协力,时间不会等待人类的蹉跎。
由此可见,WIPO刻意把知识产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用心诚为良苦。毕竟,知识产权的运用和管理正是能够贯穿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多个目标的重要工具,也是促进创新的关键。那么,究竟需要做些什么——或者更重要的是不做什么——才能立足创新创造,构建共同未来?经验和研究已经表明,创新是一个经济体能否维系其生产力可持续成长的关键,而促进创新的最大动力则是市场竞争。[6]那么,具体又应如何落实竞争?
政府的科研投入
从政策制定层面而言,所有的政府都受到有限预算的限制,其投入的各个项目之间注定会相互牵动,并延伸影响到周边的配套和资源。如何拿捏精准并保持其中的平衡,是一门精致且困难的“艺术”。不同的单位、机构、企业乃至个人(尤其是在特定科技领域具有相当名望的专家学者),总想利用各种机会为其关注的领域或课题设法争取更多的资源。政府部门通常只会看到支持者提供的各种有利证据资料,却难以接触到独立第三方的评价,尤其是不同或反对意见。当某个领域或科技受到舆情的高度关注和追捧时,这样的情况就更容易发生。这就会经常引发政府促进科研的角色定位与资源配置的争论。
当政府的科研经费向特定领域倾斜,至少能在短期内产生驱动作用,牵引其他资源和相关人才往同样的方向移动。但这无法排除各种负面状况,包括为争取政府研发项目经费而假借名目乃至进行欺诈等。同时,相对而言,其他领域将出现资源不足的问题,甚至导致高校或科研机构必须裁撤某项所谓的“冷门”部门。那么,在整体科研政策资源分配的“患寡”与“患不均”之间,究竟应如何取舍?
以医疗领域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医疗领域一直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现象。虽然政府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加强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设立了各级卫生应急指挥机构,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传染病直报和预警系统,但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依然存在短板,资源过度倾斜的状态依然持续。例如,2019年中国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中,临床占了95.3%,而公共卫生仅占4.7%,进而导致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因严重的欠缺及经年的流失,而难以满足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2019年年底发生的新冠病毒疫情,重创了全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也让上述问题更为凸显。[7]
社会环境永远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测的变量。通过政策牵引过度着重对特定领域科研的直接投入,本身寓含了相当高的风险。一旦出现某种突发状况或市场取向发生变化,政府往往很难及时跟进并调整方向。
与此相关的是,多年来,企业同高校或研究机构争抢研发资源的状况依然存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的统计,202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30782.9亿元,比上年增加2826.6亿元,增长幅度达10.1%;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其中,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为11128.4亿元(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占比36.1%[8],这意味着社会其他机构和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应为19654.5亿元。同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为23878.6亿元,由此,即使假定上述的19654.5亿元均来自企业投入,企业实际上从财政性科技经费中争取到的技术研发资金仍达到了4224.1亿元,相当于总研发经费的13.7%。除了挤压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资源,企业从政府争取科研经费用于自身研发(推定以应用型为主),还面临着另一项争议,即企业借此取得成果后如果再申请为专利等知识产权,则形同于用国家税收为自身牟利。早在2016年,就有教育部官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9]尽管目前这一情况已有一定改善,但问题仍存在。
前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范围极广,所需资源的投入浩大,且多个目标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政府的科研投入,不足以有效涵盖所有的目标和方向。因此,政府对科研的直接投入必须更加得到均衡和有效的配置,避免对特定领域的过度倾斜;同时,必须更细致地运用政府的科研资源(包括非经济性、非直接投入)作为诱因和杠杆,吸引更多各相关领域的财务、信息与人力资源的投入,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便是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运用和管理
双刃剑与细致平衡
广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包括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技术转让等领域)的价值目标如同“走钢索”,既要激励权利人,还需兼顾社会公益的微妙动态平衡。但在具体的操作上,知识产权保护并非促进创新发展的“万灵丹”,有时反而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不力或运用不当,会助长仿冒抄袭,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让一个社会的科技难以扎根,形成竭泽而渔的所谓“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反之,如果执行或运用过当,则会加剧社会的对立和纷扰,让各项科技背后的权利“碎片化”,阻碍科技的创新发展,形成资源闲置的所谓“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10]
潜在冲突的调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有些目标彼此之间存在着先天的竞合冲突,需要调和。例如,“无贫穷”和“零饥饿”被列为所有目标之首。[11]然而,当一个社会有大量人口脱贫并改变饮食习惯,增加对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与其他高价值经济作物的需求,则可能会导致粮食的分配和供应至少暂时性地出现不足,并连带导致饲料需求的大量增加和粮食价格的提升,甚至致使部分人口面临返贫的潜在风险。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放弃脱贫,而是必须在此过程中做好相关配套,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保障食物供应。[12]同时兼顾上述两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离不开创新成果与相关知识产权的重要支撑。
又如,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9个目标“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与“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三个环境与水土保持目标之间,也有相当的紧张关系,需要非常细致的资源配置和恰当的政策配套。知识产权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之间的取舍固然牵涉不少复杂问题,但如果拿捏得宜,二者亦可相辅相成。知识产权与科技对环境的影响原本是中性的,一切取决于使用者的运用方式(行为取向)。[13]2008年,IBM、诺基亚(Nokia)、索尼(Sony)和必能宝(Pitney Bowes)四家知名跨国企业组建了一个名为“生态专利共享”(Eco-Patent Commons)的专利池,任何有志于改善环境的人士都能够在经许可后免费使用其中的技术。[14]这堪称知识产权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良好范例。
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进行的一项实证调研,更得出了一个可能会令许多人意外的结论:在绿色能源开发方面,最具创新成效的竟然是一些传统的能源企业。然而,因为过去的不良形象,这些企业在试图推广其绿色能源创新技术时往往遭到来自许多环保团体的强烈怀疑和对抗。[15]以2017年为例,该调研发现,在获得“绿色专利”最多的前50名厂家当中,有7家[16](14%)一直被排除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ESG)项目之外,导致其无法获得税收减免等优惠待遇,尽管这7家企业当时一共持有6969项绿色能源相关专利,其中不乏领域内的关键技术。这不得不说是殊为遗憾之事。
直接资助与替代方案
政府的直接资助或补助通常为单次性或有期间限制,很少有对一个科研项目进行长期甚至无期限投入的情况发生。[17]因此,技术的研发与商品化经常无法脱离所谓的“死亡谷”(Valley of Death)困境,即一个科研项目进入瓶颈期后,在需要更多资源投入时,但原始资助却濒临枯竭,其他潜在的资金来源也因各种风险考量而保持观望。无数的研发项目和相关的创业计划因此功败垂成。[18]
通过立法政策提升科研积极性,则是长期内更见功效的方案。今年3月,WIPO推出了一本名为《激励技术转移:一本鼓励、认可与奖励科研与专业人员的指南》(Incentives in Technology Transfer:A Guide to Encourage,Recognize and Reward Researchers and Professionals)的新书。[19]该书虽然表面上以高校或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单位为主要对象,但也完全可以适用于企业及相关的产、学、研合作项目。
总而言之,政府在激励创新中应扮演设定规则框架的角色,其余则应交给市场去引领。两者应交互并用,但不能同时主导,否则势将发生问题。此外,对于前沿科技创新,如何让相关法规既与时俱进地对其进行规制,又避免不当扼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避免造成所谓的“科林格理奇困境”(Collingridge Dilemma),也是一项重大的考验。[20]
结论
创新需要多方因素的细致配合,最忌揠苗助长。相关的知识产权运用更需稳步拿捏,不能简单粗暴。谨再以笔者在本专栏中为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撰文中的一段话做结:
“经验法则已经表明,创新本身其实是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而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因为任何技术、知识产权都是被动的,创意的提出与后续的研发推动都成事在人。因此,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性发展’‘宽容失败’甚至‘鼓励试错’,是整个环境当中诱发创新最需要的‘催化剂’。如果企业不容许员工犯错,甚至动辄予以惩戒或要求赔偿损失,此时强调‘创新’恐怕就沦于奢谈了。总而言之,开放、竞争、公开、透明、公正、容错、尊重,是活化市场、激发创新所不可或缺的七个基本条件。”
1 “世界知识产权日”是由阿尔及利亚和中国代表提案,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00年9月在第26次会议(第12次特别会议)通过而设立的,自2001年起设于每年4月26日,也即《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正式生效的日子。首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是“在今天创造未来”(Creating the Future Today)。参见WIPO General Assembly,Memorandum of the Director General,the 26th (12th Extraordinary) Session,Geneva,25 September to 3 October 2000,WO/GA/26/2(26 July 2000),available at http://www.wipo.int/edocs/mdocs/govbody/en/wo_ga_26/wo_ga_26_2.pdf。之后每年的主题由WIPO秘书处制定,并通常于每年一月中旬发布。今年的主题中,SDGs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缩写。中文主题采用WIPO官方译法。
2 参见王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新质生产力”,《学习时报》,2024年3月18日,第二版,载于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4/0318/c40531-40197632.html。
3 同上注,习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
4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Resolution on 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Res/70/1(25 September 2015).
5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面临30年来最疲弱的五年,2024年1月9日,载于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24/01/09/global-economic-prospects-january-2024-press-release。据该报告评估,全球在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连续第三年走低,预估为2.4%,2025年可望略微回升至2.7%,但仍远低于整个2010年代的平均值3.1%;至023年和2024年的人均投资增长(per-capita investment growth)估计平均值约为3.7%,仅为前20年平均值的近半。该报告认为,除非立即调整政策并采取行动,全球经济在2020年代恐将远低于原本具有的潜力值。参见World Bank Group,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July 2024),at xv,xvii(Executive Summary),available at https://bit.ly/GEP-Jan-2024。
6 Nicholas Bloom,John Van Reenen,and Heidi Williams,A Toolkit of Policies to Promote Innovation,33 J.Economic Perspectives 163(2019).
7 李纯,郭超凯,杨程晨:从“非典”到新冠,中国该如何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载《中国新闻社》,2020年5月27日,http://www.china.com.cn/lianghui/news/2020-05/27/content_76096417.shtml。
8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3年9月18日,载于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9/t20230918_1942920.html。
9 李志民:到底谁在浪费科研经费,《中国青年报》,2016年01月26日,载于《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26/c_128669614.htm。本文作者时任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10 Garrett Hardin,Tragedy of the Commons,162 Science 1243(1968)(theory derived from William Forster Lloyd,Two Lectures on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33);Michael A.Heller,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111 Harvard Law Review 621(1998).
11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Understanding Poverty and Food Insecurity at the Household Level,Fa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Policy Brief 59(2022).
12 关于中国脱贫与食物供应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Yan Zhang and Xiaoyong Lu,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Food Security in China and Its Obstacle Factors,20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451(2023);World Bank Group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Four Decad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Drivers,Insights for the World and the Way Ahead(2022)。
13 Michael A. Gollin,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4 Harvard J. Law & Tech.193,195(1991).
14 Jo Bowman,The Eco-Patent Commons:Caring through Sharing,WIPO Magazine(Issue No. 3, June 2009),at 11,available at 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en/2009/03/article_0004.html。
15 Lauren Cohen,Umit G. Gurun and Quoc H. Nguyen,The ESG-Innovation Disconnect:Evidence from Green Patenting,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7990(2020,revised February 2024),available at https://www.nber.org/papers/w27990。该论文获得了2021年Weinberg/IRRCi Research Paper Competition首奖。
16 这七家企业分别是: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雪佛龙(Chevron)、康菲(Conoco Phillips)、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霍尼韦尔国际(Honeywell International)、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以及美国石油(U.S. Oil)。
17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曼哈顿计划”(The Manhattan Project),全程一共四年时间。以1945年战争结束时的币值计算,该计划总共耗资20亿美元(折合为2022年币值约为300-500亿美元),其中主要的开支(80%)用于秘密地点的房舍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其次是人事支出,用于研发与制造的投入只占20%左右。参见Alex Wellerstein,Manhattan Project,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available athttps://ethos.lps.library.cmu.edu/article/id/35/。
18 参见孙远钊:把创意推向市场 让创新跨过死亡谷——写在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前,《中国知识产权》第169期,2021年3月,第44页。
19 WIPO,Incentives in Technology Transfer:A Guide to Encourage,Recognize and Reward Researchers and Professionals (2024), available at 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pub-2002-en-incentives-in-technology-transfer.pdf.
20 “科林格理奇困境”是指在影响和控制技术的长远发展时面临的一个双重约束困境(double-bind problem),即:(1)信息困境——无法在一项科技的早期预期后续可能会发生的社会后果;(2)控制困境——当社会后果已经发生时,该科技已经深度融入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以致于再难对其进行有效管控。换句话说,当变化容易发生时,就相对难以预期需要做些什么;而当变化的需要凸显时,想再予以管控就变得困难。该方法学困境(methodological quandary)由英国阿斯顿大学(Aston University)教授大卫·科林格里奇(David Collingridge)于其1980年出版的《科技的社会控制》(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一书中首先提出。

